1、
《我本是高山》在正式公映后,一度甚嚣尘上的纷争反而渐次销声匿迹,争议劝退了不少观众,影片票房萎靡不振,人们疲于再复盘此前的争议与影片的好坏,这场闹剧最终以各方“多输”的结局落下了帷幕,没有人成为赢家。
冲锋陷阵的女性主义者败了,她们阻止了一部主张女性权益、反对父权压迫的电影的更广泛传播,同时还再一次被赐予了偏执狂热极度索取等“污名”。
宣传媒体似乎也败了,它的入场不但没有息事宁人,反而火上浇油,并丢掉了自己的公主桂冠。
电影的主创也败了,不管背后是商业的投机,艺术的贴金,还是赤子之心的辜负,口碑与票房的崩塌都让这场经营瞬间瓦解。
当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在影院看完这部风暴中心的电影,那些争议点令人有些不吐不快,它们为何如此细微却又能像针一样扎进批评者的眼里,激发了这场争论,而这场争论背后的舆论生态,又令人难以尽情地言说。

2、
影片一大被诛心的问题是“没有拍出张桂梅信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问题。
主旋律英模片在经历了“临死前颤颤巍巍地掏出五毛钱嘱咐道请把我的党费上交”这类尴尬名场面、及充满说教的宣传口号式台词后,已经不太可能回到批评这部电影没有信仰的部分观众所高赞期待的那样——“改成抚摸着党章及回忆入党宣誓啊”。
这种叙事策略,在又红又专、政治渗透入全民生活细节的新中国“十七年”和文革期间可以成功,但在如今可能较难生效,红色电影在失去过往计划经济放映模式、被市场化抛弃后,就已经走入世俗化、商业化的种种探索,试图摆脱那种悬浮的不被置信的“伟光正”的束缚。

事实上,张桂梅办学事业的力量源泉应该是多方面的,是孤儿院里一个个被遗弃的女婴,是民族中学里一个个流失的女学生的遭遇,是她患病后全县为她捐款给予她的感动,是她丧夫后没有家庭负担的独特条件、以及她本人执拗的个性,共同促成了她发愿要拯救大山的孩子,这些前史在片中都被抽空了,也就弱化了我们对这个角色的共情,使得海清的形似神不似的表演更加浮于表面,趋近空洞符号。

而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信仰,像是她发愿之后的一种借力,那几年办学无门的张桂梅在2007年迎来转机,曾经反对她办女高的杨文华直言“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十七大代表了,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通天了”,各级压力之下,女高得以建成,成为全国独一份没法复制的意外之举。
电影点到为止地拍摄了宣誓、升国旗、唱红歌等场面,但更多地还是想立足于她对现实的痛感,对大山女孩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想要救救孩子的朴素愿望。
被大家奉为正面教材的《焦裕禄》正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的感人不在于是否有宣誓的豪言壮语,而是目睹群众的水深火热、反派干部的冷漠无情,身处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劣、身边家人的委曲求全,以及麻绳专挑细处断的病魔缠身,所有这些做到极致的苦情因素,共同形成了麦基在编剧圣经《故事》里说的“反对主人公的对抗力量越强大复杂,人物和故事必定会发展得越充分”。
而所有这些方面,在《我本是高山》中都显得过于“克制”:对大山女孩最惨烈的遭遇的描写,是山月被迫嫁给40岁男人并被家暴而死,但除了最后一个盖着白布的尸体镜头,这段遭遇全都靠台词转述;真正的反派一个也没有,基于现实原因对教育局长的描写自然是先抑后扬,辞职的女老师也不足以对张桂梅构成威胁,从山里闯入女校试图“抢”走山英的男人们甚至都没有动手,他们在权力结构里的暴力性本应借此视觉化地展现出来;而张桂梅的病情除了贴胶带、吃药外也没有类似焦裕禄试图用非人的意志去压制病痛的那种煽情。

或许正是这份克制,才导致影片缺乏了部分观众渴望看到的精神力量的高度。这种克制可能是受制于拍摄许可的禁区,可能是主创自以为更高明的策略选择,而综合作出的选择,但终究没有将影片导向更优的层次。但这部勉强及格的影片在最后依旧实现了煽情的效果,山英山月这条故事线拯救了影片对张桂梅等角色流于表面的刻画,以其真实可感的悲剧宿命与人物弧光成为全片最催人泪下的情绪出口。

当然,如果是更有艺术个性表达的导演去拍,如同诺兰拍《奥本海默》呈现一个被政治与道德多重审判剥得精光的原子弹之父,尽管能突破某些低级的套路,也只会呈现一个更多复杂、多面、矛盾、更加冒犯大众常识的新张桂梅。对于英模片来说,也许平庸就是它最好的归宿,是让上层与民众都皆大欢喜的最大公因数。
3、
而女性观众所聚焦的几个争议点,似乎都不太足以成为攻击影片矮化张桂梅、污名化女性的证据。显然,主创低估了它的受众对权益的索取、对男性主创的苛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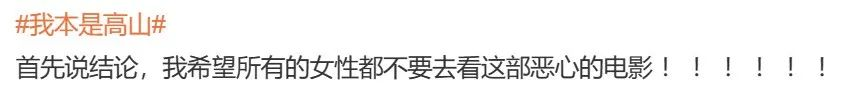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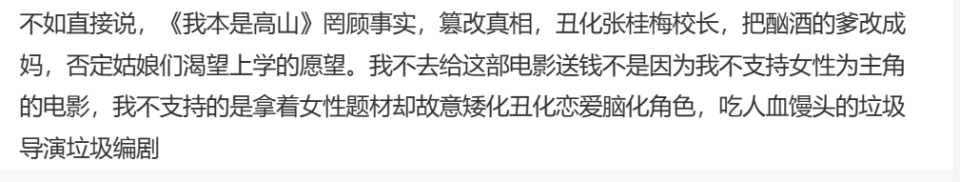
但考虑到这是一部书写女性反抗父权压迫、“顺天改命”——女权主义者谴责影片“逆天改命”的宣传语——的电影,它的某部分受众本身也在参与影片所书写的这种反抗叙事,那这种“现实介入电影”的激进姿态,又似乎变得情有可原。
《人物》杂志此前对张桂梅的采访近期被挖出来广为流传,文中展示了张桂梅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丈夫生前多才多艺、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给她做饭,两人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去市里开会,当天赶回来和她吃饭,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她穿着漂亮裙子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跳舞,被调侃为老妖精也乐在其中……”
与新闻镜头里愁眉苦脸、形销骨立,让人又敬又畏的小老太形象不同,原来以前的张桂梅的生活,是这样冒着粉红泡泡,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她那时候的飞扬烂漫,这样动人的素材,电影主创怎么能不用?于是可能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胡歌作为亡夫的出现,可惜的是主创没有用好这抹亮色,反而拍得颇为苦情。

但胡歌的角色,终究是抚慰了困境中的张桂梅,他的功能是还原一个被宏大主流叙事遮蔽的多面个体,将一个新闻媒体中的钢铁般的半神还原为一个更有血有肉的人,且有据可查,符合张桂梅本人对亡夫深情的追忆事实:她在丈夫死后抱着骨灰盒走在路上“寻死”,她说自己千方百计申请从大理调到更偏远的华坪任教,是因丈夫去世后的逃避和自我放逐。
而胡歌的角色功能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取代所谓信仰作为张桂梅力量源泉,他仅仅是张桂梅在私密空间里自我疗伤的安慰剂,是“疗愈者”而非注入神奇力量的“赋能者”,所以她也会在追忆完丈夫后依旧自暴自弃地对学生们吼道“女高没了”“今天是散伙饭”。
而最可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张桂梅濒死之际的梦境里,她几乎就要追随胡歌的亡灵而去,但转而却被学生们齐唱的《红梅赞》歌声感召回来了,亡夫从此消失,他作为“工具魂”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对于张桂梅来说,可以真正相濡以沫相互成全的,不是亡夫而是眼前这帮孩子,她于她们并不是单方面付出的关系,而是她们也在拯救她孤苦无依的生活、成就她登上精神上的高山。
因而,亡夫的出现似乎有其合理之处,不能粗暴地理解为矮化、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剥夺,对男性的跪舔。这个角色的设计尽管是浅薄的、套路的,但却与影片是否拍出张桂梅的信仰,没有直接关系。
另外,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观众角度去看,这部影片备受争议的两个女性角色——酗酒的母亲与撒泼的女老师,其实都不过是将角色当作工具符号的套路化叙事的产物。

对于酗酒母亲,主创早已解释过她承担的“被拯救的两代女性”的角色功能与事实存在的现实原型,但依旧得不到原谅。确实,这个角色在影片中一度有失真的观感,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都市里的流浪汉而不是大山里的母亲,但这是创作水平层面的问题,站在既定的立场上,批评者可以质问为什么不是“拯救被酗酒男性家暴的母亲”,但问题是,主创也没有未卜先知地预料到,自己一笔不太高明但直切主题的创作,会被归咎到“丑化女性”的诛心上。

对于撒泼的女老师,这个角色更大的问题则在于极度脸谱化,以一种“作女”的形象反衬张桂梅的无私,对这个角色的丑化也超出了现实中对常人的道德要求——打工人早就苦“996”久矣,这位老师忍受不了张桂梅“507”、干涉穿衣自由等“非人化”管理手段,怎么就要被塑造成招人嫌恶的反派呢?

但批评者的问题同样聚焦在——凭什么反派是女老师不是男老师?可是女性主义就是删除一切正面男性角色、拒绝一切负面女性角色、否定女性对男性的情感诉求坚决厌男吗?
基于全片来看,影片本身最高潮的冲突段落就是全校女生一起支持山英对抗从山里闯入女校的父权既得利益男们,影片在主线上从未偏离支持女性这一根本立场。

显然,这是激进派对温和派的宣战——哪怕是在女性主义的阵营里,也是分流派的。如果主创不能将自己拔高到激进派的“思维高度”,那就无法与这部分观众同频共振,那就可能面临被冲击的命运,这也为以后的女性题材电影的创作敲响了警钟,也加上了紧箍咒。
4、
比这部电影本身更值得忧虑的,是这场论战背后的舆论生态。
它的导火索有女性主义对自身权益的索求,有电影创作者面对批评的失控,有主旋律倡导者对批评者成分的“定性”,表面上多种力量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缠斗,背后是日益撕裂的社会生态,与被某种死灰复燃的狂热及其相应话术所裹挟的头脑。
不管是哪一方的立场,他们似乎各自拥有全部的道德优越性,以正义的名义消灭一切反对派;他们奉行非黑即白的思维、以立场先行再去举证,用可能令人费解的逻辑勾连因果;他们以摧枯拉朽的运动,各自党同伐异,用“泼脏水”“丑化”“污名化”等话术,揣摩与制造假想敌,互相倾轧。
参与论战的人似乎只需要病毒式复制粘贴“僭主”的观点而不需要看片和自己生产内容,就能投身到激情燃烧的舆论战场,获得出征的快感、道德的满足感。而养育出这个舆论土壤的人,也在体会被它反噬的滋味。

有人甚至玩梗说,“终于理解当年为啥要批判《武训传》了”,这种观点竟也得到认可与传播,《武训传》乞讨办义学的武训被视为向封建势力和文化低头献媚,尽管当年的《武训传》最初试图停留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层面,但箭已出鞘,它奠定了此后电影乃至文艺批判的范式,令艺术创作的根本变成服务政治。
在那之后全国电影产量从1950年的29部,下滑到1951年到1954年4年合计才16部,没有电影人能经受得起显微镜般主义先行的审视,只能自绝手艺,如果说电影没有那么重要,别着急,下一个被全面侵蚀的就是其它日常娱乐与生活的私人空间了。
一些曾被视为常识的东西在悄悄瓦解,一种陈旧的价值观重新占领有些人的头脑。这场论战一方面继续蚕食我们言说的舆论空间,一方面又挤压电影表达创作的尺度令人自危,不得不说是一个多败俱伤的结果。